平台友情提醒:凡是以各种理由向你收取费用,均有骗子嫌疑,请提高警惕,不要轻易支付。
悲剧|马勒和他的第六交响曲
在马勒的全部交响乐创作中,《第六交响曲》非常独特,音乐界和众多“马勒迷”一直对其抱有浓厚的兴趣。
这部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首先让人大开眼界:马勒使用了交响乐创作以来**的管弦乐队,“超级四管乐团”的扩大版,尤其是八个圆号和六个小号。通过圆号、四把长号、两把竖琴和众多打击乐器的运用,作曲家大力拓展“交响世界”的意图昭然若揭。他显然是在刻意构建一种新的交响式宏大叙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表达强烈的愿望。从作品的体裁和面貌来看,《第六交响曲》是马勒最接近古典交响曲传统的创作:纯器乐的音乐表现、四乐章组合的整体结构、前两段奏鸣曲形式“大乐章”结构思维的展现,强调以“主调”为核心的A小调整体布局的调性逻辑联系。当然,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用如此庞大的管弦乐队,回归交响曲的传统和典型表达,马勒在《第六交响曲》中到底想表达什么?换句话说,这部“交响杰作”(全曲约80分钟)到底传达了作曲家怎样的艺术诉求?
阿巴多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悲剧”
第六交响曲也被称为“悲剧交响曲”。马勒本人是否为这部交响曲起过这样的“标题”,并无明确记载,但他似乎并不介意别人称其为“悲剧交响曲”。熟悉创作的人都知道,“揭示悲剧意识的“生与死”始终贯穿于马勒的交响乐观念和作曲实践之中。正如勋伯格所说:“事实上,一切将形成马勒特点的东西都已经表现出来了。”在**交响曲中。在这里,他的生命之歌已经奏响,只会在以后展开。 ,呈现到**。在这里他表达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和对死亡的思考。始终与命运作斗争……”既然这是对“生与死”思想的持续冲击和艺术“回应”,那么在前五首交响曲各具特色的悲剧性展现之后,又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第六交响曲》的悲剧精神具有个性化的呈现和独特的意义吗?
总的来说,如果说马勒早期交响曲创作(**至第四交响曲)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上,那么从《第五交响曲》开始的中期创作则更多地体现在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上。它大多反映了作曲家内心的痛苦和激烈的挣扎。
上海交响乐团排练
《第六交响曲》创作于1903年和1904年夏天,整部作品的管弦乐配器于1905年完成。该作品于1906年3月与马勒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进行“试音”,并正式被首演于1906年5月27日。据马勒的妻子阿尔玛介绍,马勒在创作《第六交响曲》时特别用心。并完全沉浸其中:“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能像第六交响曲那样直接地出现。在他内心的最深处。那天我们都哭了。这首音乐和它的预言深深地触动了我们……”阿尔玛的记忆中还特别提到,在正式首演前的最后一次排练中,马勒对他的音乐印象深刻,即使回到休息室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兴奋。
西蒙·拉特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悲剧”
马勒对自己的交响曲如此动情,确实耐人寻味。尤其是当这种情况与马勒此时的事业和生活处境联系起来时,其深刻的意义就更值得细细品味和思考。作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艺术总监,马勒达到了职业生涯的**。 1902年,他与维也纳艺术圈最耀眼的社交名流阿尔玛结婚,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女儿。他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暖,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然而,如此美丽的场景却催生了具有强烈悲剧感的《第六交响曲》,这说明马勒在思想上积累和精神上扎根的内在悲剧意识和人格心理并不是由于外在个人素质的提高而形成的。生活环境。改变。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马勒内心的焦虑和精神压抑也越来越强烈。
马勒生来就有一种昂扬的气质和孤傲的气质。他的犹太血统和文化背景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孤独心态和悲剧意识。即使在登上了维也纳乐坛的头把交椅,成为国家歌剧院的艺术总监,成为整个维也纳文艺界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之后,马勒内心的孤独和不安全感也从未消失。 “我是一个三重无家可归者,在奥地利被视为波西米亚人,在德国被视为奥地利人,在世界各地被视为犹太人。他是一个入侵者,永远不受欢迎。”正是这种失去精神家园的压抑、悲伤和怨恨,不仅导致了马勒永恒的精神留恋和悲剧性的不归属感,也激发了他的孤独感。奋力拼搏。
值得注意的是,马勒在创作《第六交响曲》的同时,还创作了为乐团伴奏的声乐组曲《死去的孩子之歌》。阿尔玛对马勒选择吕克特的诗作配乐感到不满,因为这位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写这些诗是为了哀悼自己孩子的去世。可以想象,当时患有产后抑郁症的阿尔玛,当她得知丈夫写了一首如此不祥的歌曲时,感到既害怕又愤怒。不幸的是,马勒五岁的女儿玛丽亚几年后死于猩红热和白喉。尽管马勒对女儿的死深感自责,心态几近崩溃,但他对死亡形象难以摆脱的痴迷,却让他以超验的哲学意义审视“死亡”。正处于创作之中的马勒,将他对“生与死”这一哲学命题的理解转化为强有力的交响话语。他坚信自己只能用纯器乐的能量来展现现实的批判和潜在的悲剧。顽强奋斗的“英雄”情怀。 《第六交响曲》正是这样一部思想复杂、意义深远的“交响悲剧”。可以说,马勒本人就是这场“悲剧”的“主角”。性与无形的姿态出现,像英雄一样驰骋在人生的战场上。
**乐章开头的音乐扣人心弦,直接引入进行曲营造出重压下的紧张气氛。如果说马勒《第五交响曲》**乐章中的葬礼进行曲还具有哀悼的抒情性和追忆的舒缓性,那么这里的音乐进行曲就完全抛弃了温暖,变成了一种强烈的压迫感,显得咄咄逼人。在此背景下出现的A小调主旋律,形成一种威胁而傲慢的姿态,如同末日的凝视。 F大调的次要主题也称为“阿尔玛主题”。渐进的旋律流动充满了音乐美感,而伟大的抒情表达也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这位维也纳文艺界女神的“性格方向”。事实上,马勒作为这场“悲剧”的“主角”,也在此时“出现”,因为这里激情的涌动也可以理解为马勒在对抗厄运侵袭时对生命的呼唤。马勒显然非常重视阐述中这两个主题的“意象”对比和情感承载,因此他利用古典交响曲中阐述的表演套路,将他在交响曲中刻意强调的“意象”再次呈现出来。从头开始重复的形式。 “生”与“死”较量的想法。
马勒鲜明的“主观意识”也可以从中间两个乐章的音乐创作中感受到。虽然谐谑曲乐章仍然保持着作曲家所写的体裁特有的质感和韵味,但这类音乐中朴素生动的民俗风情却被厚重而有力的力量冲击力所取代。它所呈现的是一种酣畅淋漓、有趣又带有悲剧意味的东西。由于这首谐谑曲宏大、内涵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乐章的悲剧音乐。其流派特征和音乐性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艺术扩张所带来的变化。具有戏剧意义的“灵活”风格。与谐谑曲乐章基于体裁特征的艺术改造相比,该乐章是传统慢板乐章抒情表达的延续。在这里,开场和结束时丰富的抒情性被刻意与前两个乐章的沉重、严厉和激动人心的动态分开。马勒用极其细腻的管弦乐笔触和丰富多变的音色修辞来表现“角色”的理想化。那里的风景,洋溢着对美好生活的真实渴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极其丰富的抒情魅力和深刻的寓意都使这首曲子成为马勒交响曲中最迷人的慢乐章之一。
于峰指挥上海交响乐团
毫无疑问,马勒独特的纯乐器思维和超强的艺术表现力在第四乐章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任何细心聆听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马勒作为“音乐思想家”的角色和声音。在这个长达半个小时的长乐章中,作曲家的“存在意识”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乐章开始时感人的幻影般的翱翔(这是引导和贯穿最后乐章内涵的重要音乐思想)到荡气回肠的“最后牺牲”和“死亡”意象的逐渐淡化在全曲的最后,马乐用自己熟练掌握并创造性运用的“管弦十八技”,全力表达了英雄情怀的悲剧精神。有力扩展的奏鸣曲形式带动了丰富多彩的交响叙事,马勒对强烈自我意识的创作追求达到了晚期浪漫主义声音建构所能达到的艺术表现的**水平。无论是音乐高潮时的两首突破性的金曲,还是多个段落中出现的各种精致而富有想象力的音形,我们都能体会到渗透作曲家个性的生活方式。
马勒在《第六交响曲》中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他的**目标:创作出展现真实内心的个性化音乐,不懈地探索承载着悲剧精神的人生哲学的意义。
最新! “馄饨皮”上座率调整为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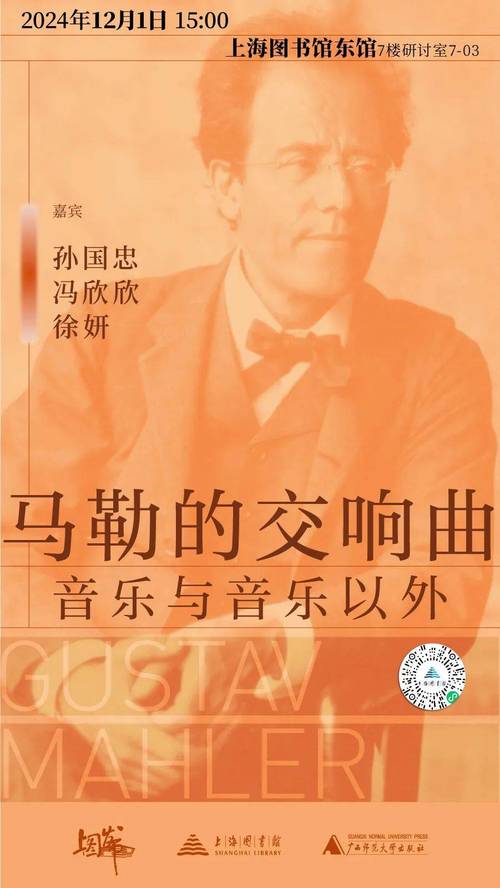
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经历了30%→50%→75%的上座率限制,今天终于达到了100%。
还没有买到这场演唱会门票的朋友们,机会来了。 “于峰演奏马勒第六交响曲”音乐会现已开放增座。长按二维码抢票,动作要快!
《音乐家·可爱》
音乐家粘土娃娃:“音乐之父”巴赫
三月是“音乐之父”巴赫的生日
在这个温暖的春月里
让我们一起庆祝巴赫和音乐
点击购买
性能信息
于峰演奏马勒第六交响曲
时间:2021年3月21日20:00
地点: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主厅
票价:/380/180
额外座位热销中
指挥:于峰
上海交响乐团
曲目:
*演出曲目以现场表演为准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