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还是祸?我们来谈谈《电子商务法》对电商平台的直接影响
2018年8月31日,经过三轮全民征求意见、四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五年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终于在万众瞩目下出台。
大家已经注意到,《电子商务法》的立法博弈贯穿始终。与部委主导立法的一般做法不同,《电子商务法》从一开始便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牵头、国务院12个部门组成的起草组负责起草。即便如此,2011年至2013年,原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均出台了相应规章。《电子商务法》初稿据称是代表企业声音的行业协会提纲、学术界提纲和代表监管部门立场的原国家工商总局提纲的综合体,至今已修改数十次。
2018年8月16日,在全国人大四稿前举行的立法咨询会上,阿里巴巴、腾讯、网易、京东等互联网巨头均派代表出席,马云亲自代表阿里巴巴参会,也体现出国内电商巨头对《电子商务法》的高度重视。
《电子商务法》第四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前,未征求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意见,中国消费者协会罕见公开批评《电子商务法》立法程序存在缺陷[1],并表示《电子商务法》第四稿拟将电子商务平台的安全审查义务由“承担连带责任”改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存在严重风险[2]。
由此,《电子商务法》草案第38条关于电子商务平台安全审查义务的规定,发生了从“连带责任”、“补充责任”到模糊的“相应责任”的重大转变。
总体来看,《电子商务法》明显是消费者、电商平台、监管部门等多方意志博弈的结果。这部法律将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其对整个中国电商行业的影响不可估量。
本文试图简单分析一下该法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直接影响。
第 1 部分
电商本源正在清理,合约电商正在被清理
此前,官方对“电子商务”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地方淫秽色情易场所往往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地方政府也将地方淫秽色情易场所的交易额作为电子商务纳入统计范畴。因此,国内曾有“商品和服务电子商务”和“合同电子商务”的常见分类。例如,国家统计局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调查[3]显示,2017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9.16万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中,商品和服务电子商务交易额21.83万亿元,同比增长24.0%;合同电子商务交易额7.33万亿元,同比下降28.7%。
但这一切将随着《电子商务法》的出台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电子商务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或者其他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
第 46 条明确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为经营者之间提供电子商务服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通过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也不得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
这将基于合同的电子商务完全排除在电子商务的范围之外。
这些规定显然是针对地方交易场所此前存在且目前仍然存在的“类证券期货”经营行为,也是对2013年12月23日证监会、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工商总局、银监会发布的《关于禁止以电子商务名义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活动的通知》的再一次肯定,从此电子商务仅指商品和服务的电子商务。
第 2 部分
网上卖家的商业登记和纳税义务
自然人以个人身份在淘宝等第三方C2C平台开设网店,是否需要办理工商登记?
2010年,原国家工商总局出台了《网络商品交易及相关服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虽然规定通过网络从事商品交易及相关服务活动的自然人“符合登记条件的,应当依法申请工商登记”,但实质上明确免除了自然人网络店铺向工商机关登记的义务[4]。
而即将于2019年1月1日生效的《电子商务法》则直接推翻了这一规定。立法者的本意依然是以登记为原则,以不登记为例外。因此,《电子商务法》第十条最后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同时又留了一个小窗口,即“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艺产品、个人利用自身技能从事便利劳务和零星小规模经营,依法不需要办理许可的,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需要办理登记的”。也就是说,除极个别例外情况外,未来几乎所有的电子商务网络卖家都需要办理工商登记。
此外,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此次也将得到彻底解决。虽然从法律角度看,无论是网络销售,还是线下实体店销售,都发生了应税货物和服务销售行为,应当按规定缴纳税款。但在实际税收征管过程中,线下实体店经营地点固定,始终处于地方税务机关的监管之下,即使不开具发票,也会采取定额等方式进行税收监管,因此很难完全逃税。但对于线上电商而言,由于网络销售产生的交易数据主要集中在电商平台上,加之我国税收管理的登记地原则,地方税务机关无法对电商平台上网络卖家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如果消费者在电商销售过程中不主动索要发票,就会给网络销售企业逃税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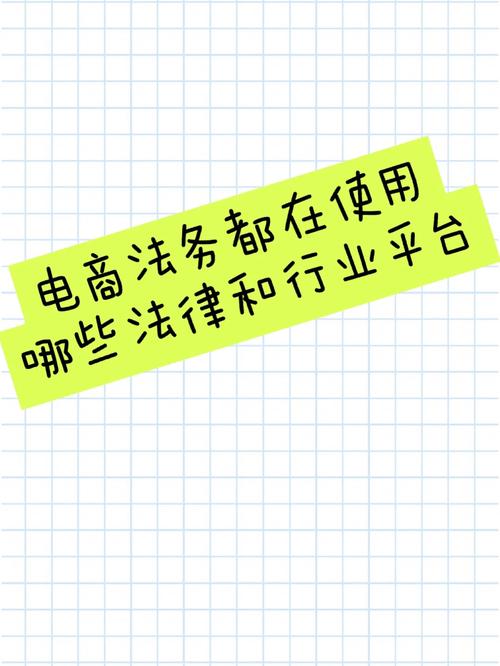
作为电商平台,京东、天猫、苏宁易购等平台的B2C电商卖家很多都已办理税务登记并正常纳税,相比之下,C2C电商平台个人卖家开设网店不纳税的情况却相当普遍。依法规范电商销售、保障网络销售与实体销售公平竞争的呼声越来越高。《电子商务法》第十一条首次明确要求电商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即使电商经营者无需按照第十条规定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在首次纳税义务发生后,仍应当依照税收征管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办理税务登记,如实申报纳税。
网络卖家将需要到工商局登记,履行纳税义务。C2C电商平台上大量自然人网店将需要到工商局登记,这些网店将需要依法纳税。这也意味着,以自然人网店名义不纳税的电商企业避税福利将告一段落。这两项条款无疑将成为《电商法》实施后对电商发展影响**的重要条款。
由于经营模式不同,不同电商平台受到的影响也不同。B2C电商平台受影响相对较小,受到**影响的无疑将是淘宝、拼多多等C2C电商平台和美团、滴滴等O2O企业。《电商法》若严格执行,C2C电商平台店铺运营成本的上升势必导致个体卖家的流失,对整个C2C电商平台的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业内甚至有“电商法如果通过,对阿里巴巴来说就是一次挫折”的说法。
第 3 部分
电子商务平台的审计和安全义务
根据《电子商务法》第27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的审计义务包括对平台内经营者身份、地址、****、行政许可等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审查并定期核实、更新。第28条进一步规定,电子商务平台应当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身份信息。我们认为,这样的审计义务,特别是定期审计、更新的要求,无疑将大大增加电子商务平台的人力、物力投入,从而增加其运营成本。
至于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则应源于《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相关规定[5]。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行政责任包括责令停业整顿、处200万元以下罚款等。滴滴、美团、携程、OFO等通过互联网销售服务的电商平台,提供网约车服务、外卖服务、酒店旅游服务等,这些企业比单纯的商品电商平台更直接接触线下社会生活,因此恶意事件发生的频率更高,面临的安全保障压力更大。随着滴滴顺风车撞死温州女孩案的发酵,社会舆论有加大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趋势。如何合理界定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有待执法和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
第 4 部分
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
电商平台的责任是立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在审议过程中也存在广泛争议。《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1款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依法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第 2 款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未尽到平台内经营者资质审核义务、未尽到消费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正是第38条第二款这一“承担相应责任”的条款引发了热议。《电子商务法》第四稿原本是想将电商平台的安全审查义务由之前的“承担连带责任”改为“承担相应补充责任”。然而,“温州女孩滴滴搭车杀人案”改变了立法方向,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暴露了滴滴平台对司机背景调查敷衍、客服安全保障不力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立法者将电商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的审查义务或未尽到对消费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限定为“补充责任”,立即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反弹。有人指出,《电子商务法》一出台,就面临与《食品安全法》第131条[6]的法律冲突。甚至有人公开质疑:滴滴搭车杀人案这么快就被人遗忘了吗?中国消费者协会于2018年8月29日发表严正声明称,此项修改将大大降低电商平台的责任,对《电子商务法》构成严重风险,希望将“补充责任”改回“连带责任”。
立法者最终将“补充责任”改为“相应责任”,虽然措辞模糊,避免了争议,但实际上回应了舆论的高度关注。这一立法技术性回避,也将个案中电商平台责任的认定权交给了执法机关和人民法院。但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执法人员和法官对同一类案件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做出不一致的责任认定。
第五部分
电子商务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
《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第八十四条进一步规定,电子商务平台在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时,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承担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电子商务法》在实践中对“通知—删除”规则(又称“避风港规则”)进行了修改。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一般认为,“通知—删除”程序实施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免除责任,并声称进入了“避风港”。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电商平台上的商品侵犯其知识产权的,可以告知平台,要求平台经营者移除该商品。电商平台经营者在收到前述权利人的通知后,一般应先评估侵权的可能性,若侵权可能性较大,应立即采取措施[7]。实践中,若电商平台认为侵权可能性较小,一般会直接驳回权利人的投诉或举报。
《电子商务法》直接修改了“通知-删除”的游戏规则。《电子商务法》第42条规定:
知识产权权利人认为其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的,有权通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
通知应当包括侵权行为发生的初步证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收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将通知转发平台内经营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对损害的扩大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