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友情提醒:凡是以各种理由向你收取费用,均有骗子嫌疑,请提高警惕,不要轻易支付。
梁磊:周文重的启示
以下文字节选自《汇流:周文中音乐集(附CD)》,主编:梁磊,副主编:罗勤,翻译、审校:蔡良宇,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
周文重的启示
——庆祝周文中教授九十华诞
梁磊
周文中先生与梁磊合影
一个人的音乐作品和文章往往蕴含着作者一生的分量。他生命的厚度、思想的深度、他的人文关怀,都会从他写下的每一个笔记、每一段文字中闪现出来。
1941年,18岁的周文重和一群年轻人在逃亡过程中试图穿越日占区翻越浙江天台山。逃亡途中,他听到了天台山山顶的狂风和三门湾街头青年同胞被枪杀的残酷枪声。几十年后,风声和枪声仍然进入他的噩梦,折磨着他,激励着他。
周文中先生的音乐作品和文章在用现代音乐语言表达深刻的哲学和亚洲艺术美学的同时,也常常传达出一种生命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源于他的亲身经历。除了音乐创作和文字写作,他还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文化保护工作、帮助扶助青少年等方面,这些都与他自己在逃亡时期的经历有关,也与那些冒着风险的无名人士有关。他们的生活在危机时刻。他与当地农民的感激之情是分不开的,他们保护他免受危险,并为此献出生命。
周先生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汇点。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如果处在不同时代、文化、学术领域的交汇处,往往能产生新的想象,发现新的路径。周先生是一位融合西方现代音乐语汇再现东方美学的文人。他是一位以声音为笔、以声音为墨的“声音书法家”。
周先生从小就接受中西融合的教育。他听人们唱诗,被音乐的表现力深深折服。后来,通过研究书法和古琴,他认识到中国诗歌和书法的变化,其途径和效果是相似的。他从中国哲学和艺术中探索并融合了一种自成体系的音乐语言。这种语言有其固有的语法,就像书法的规则一样:每个人都会使用它,但每个人的表达方式都不同。
周先生的音乐创作对我国音乐产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是20世纪中叶**批开创亚洲传统美学与西方前卫技法相结合的作曲家的杰出代表。他与韩国的尹伊桑、日本的武满彻等人一起开辟了现代音乐的新河,成为**位受到西方音乐界广泛重视和尊重的家。从上世纪中叶到现在的近60年里,他乐于助人,一丝不苟地贯彻落实自己的个人意见和主张。他于1960年创作的木管乐队作品《隐喻》,首次尝试了“模式”的概念,开始了对这种融合中国易经哲学原理和书法艺术原理的音乐语言的长期探索。在长笛与钢琴二重奏《飞草》(1963)中,他将这一概念系统地发展为“节奏模式”;在打击乐四重奏《孤影》(1989)中,他从音值和音型方向的角度进行了探索;近期作品有弦乐四重奏《浮云》(1996)、《流泉》(2003)、六重奏《浮云》(1996)《霞光》(2007)等,结合了他对书法艺术的研究和对位法。巴洛克时期。最新的“青松”室内乐系列包括“青松”(2008年,韩国传统乐器)、“歌唱松”(2009年,西洋乐器)和“青松”(2012年,中国乐器)。 《为传统乐器而作》是周先生多年研究亚洲音乐以来**首为亚洲传统乐器创作的作品。可以说是对一幅抽象作品的三种完全不同的解读。这里直接比较了这三种音乐传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早期作品《渔歌》(1965)堪称配器的典范,很多人学习甚至模仿他。这些作品的影响力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话题。他早期的音乐实践使得许多追随他脚步的亚洲作曲家的音乐实践成为可能。
作为老师,周先生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曲系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翁佳利、陈毅、周龙、谭盾、盛宗良、葛干如等一批重要的亚洲作曲家获得了在美国深造和发展事业的机会。他的作文教学对这些学生产生了直接影响,并继续影响着美国各地高校的下一代亚裔学生。这群音乐家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成功与周先生的教导密不可分。周先生自己的创作是“十天画水,五天画石”。每个声音都有表达和逻辑。它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装饰,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精炼而成。的。他对自己和学生都有这样的要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教导和支持年轻一代作曲家,他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现代音乐的整个面貌。
作为20世纪重要作曲家埃德加·瓦雷兹的弟子,周文重先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保护、研究、分析并严格修改和完成导师的手稿。师从瓦雷兹无疑成为影响周先生思想观点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也正是因为周先生的努力,有关这位作曲家的许多重要资料得以保存下来,让20世纪的音乐史得以保存这份不可估量的财富。这种一生回馈恩师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也是我们后辈的榜样。
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苏醒、逐步打开国门的历史时刻。作为一位热心的文化使者,周先生通过197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的“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往返于促进中美文化的互动。一方面,他向中国观众介绍了美国现代艺术。另一方面,戏剧、音乐、美术也邀请了很多中国人才访问美国。这些交流活动开拓了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力,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1990年起,周先生通过“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参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保护工作。对建筑、艺术、民间艺术家、生态环境(含高黎贡山)等当地物质和非物质艺术遗产进行多方位保护。在巍山等历史名城,在交流中心的参与下,珍贵的历史建筑得到了修复和保护。当云南民族大学扩建为云南民族大学时,周先生帮助建立了新的教学项目。邀请本土艺术家参与本土青年人才培养,传承和弘扬本土文化尤为重要。只有植根于本土文化的艺术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性,才能对世界文化做出真正的贡献。这种教育思想体现了周先生的远见,也体现了他对当今西方文化对世界殖民的批判,以及他希望亚洲的年轻人放弃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培养真正的自信。正如他自己所说,“云南的文化保护工作是我的作品之一”。
在此,请允许我补充几段我与周文中先生的个人交往的片段,以便读者了解我接触到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1990年来到美国上高中的,虽然与周老师交往密切的亲朋好友很多,而且我早就听说周老师欢迎大家,对待学生慷慨热情,但我还是十六年来不敢打扰他,多次谢绝。感谢您的好意介绍。因为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担心和他见面会浪费他宝贵的时间。但我从心底里一直把周文重先生视为我的老师之一。我读过他的文章和著作,对他的著作非常熟悉。直到2006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位,我才觉得终于到了向周老师请教的时候了。
果然,周先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你一见到他,你就会受到他的考验。我们**次见面时,他给了我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线什么时候不是线?” (什么时候一条线不只是一条线?)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了他对东西方艺术中线条运用基本原则的关注。 。几何线条是平面的,而书法中的线条则有体积、质感、多维性。只有理解了这个概念,才能理解古琴音乐与书法的内在联系,才能理解线条在周先生音乐创作中的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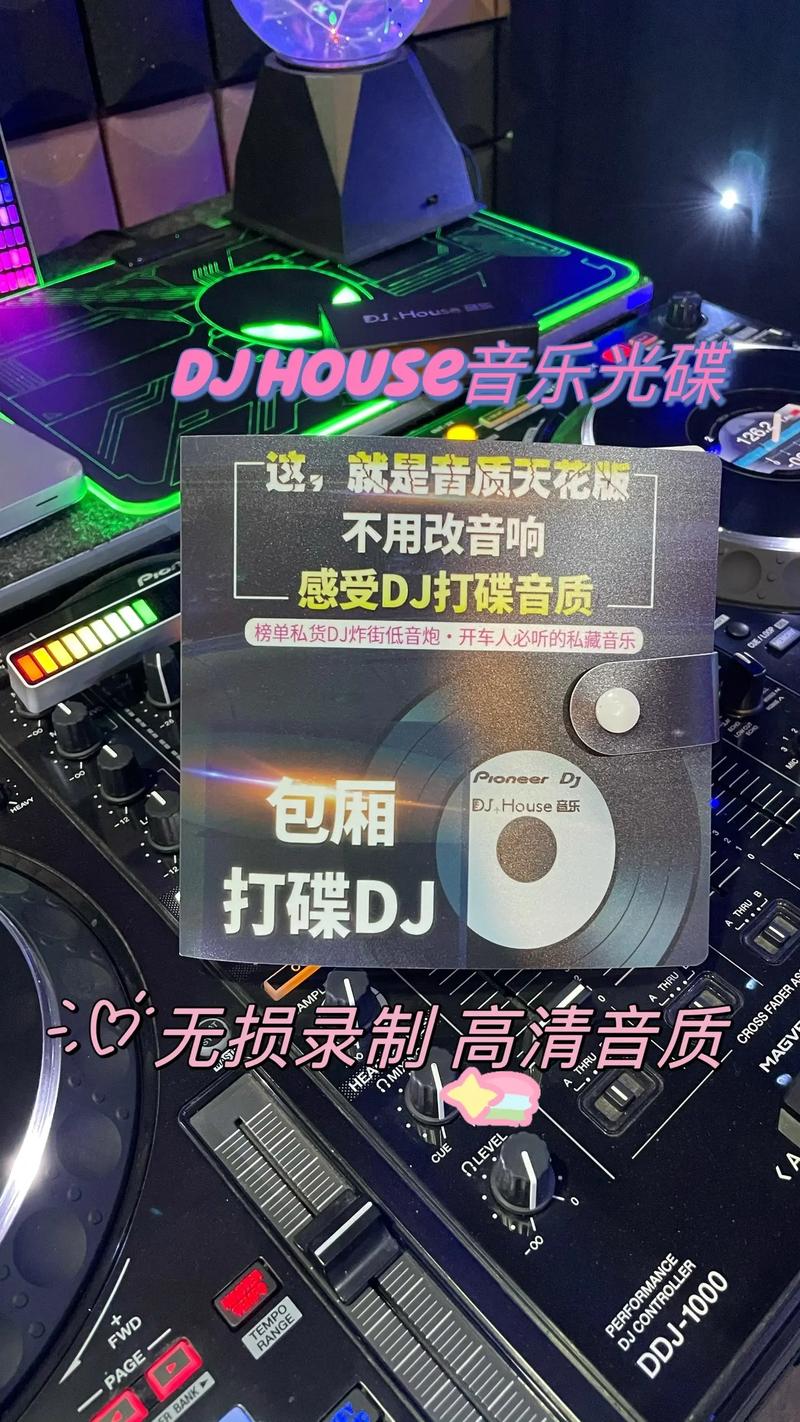
如果我们研究他早期的钢琴与笛子二重奏《飞草》和他最近的两首弦乐四重奏《浮云》和《流泉》,我们可能会发现,对于周先生来说,音韵和墨墨都是线条。艺术。从更抽象的角度看,一丝思想或情感就像线条一样自然地诞生在灵魂的纸上。书法中的每一点每一行都饱含着作者丰富的情感。这些具体和抽象的线条是不断变化的:它们或粗或细,或干或湿,或暗或亮,或慢或快,或轻或重,或直或弯。它们源自不同的内心触动,有着变化无穷的表情,都在周文重的笔下化作音符。这些带有不同情感的线条纵横交错,构成了一首声音的交响乐。也是一首融合了中西艺术精髓的多行赋格曲。只有在对中西传统的高度理解的基础上理解台词的概念,才能理解周文中音乐作品中的智慧和发明。
我深深体会到他对青少年的关怀。我多次去他家拜访,交谈后,他经常亲自做一道道中国菜。我的妻子周以安女士热情好客。我和周先生围桌而坐,三人围桌而坐,必然要有酒来陪。这时,严肃的周先生变得轻松起来,他和妻子互相开玩笑,妙语连珠。我觉得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天真、幽默,甚至调皮!这样的气氛总是让我忘记了已经是深夜了,错过了回家的火车。
当我的儿子出生时,周先生和周太太立即送来了一件小毛衣和一头小牛——那一年是牛年,我的儿子是牛年出生的。
2009年12月,我去纽约参加纽约爱乐乐团首演我的作品。我怕打扰他,而且天又冷!我曾多次劝周先生不要亲自来听音乐会。可当我走出地铁站的时候,却看到周先生和周太太互相搀扶着,顶着寒风一步步朝音乐厅走去。至今,每当想起这一幕,我仍然十分感动。
我们必须尊重我们自己的中国作曲家。这也是我发起本书编写工作的初衷。在编辑出版这本选集时,我有以下想法。
一:重要的作曲家往往能写出好文章。原因很简单:虽然深刻的思想不一定能产生深刻的音乐,但没有深刻的思想就不可能产生深刻的音乐。我们不谈19世纪之前的事情,只看20世纪。我特别尊敬的作曲家大多都有发人深省的文章:欧洲的美国艾夫斯、科普兰、凯奇、卡特、布列兹、施托克豪森、莱赫蒂、贝里奥,日本的武光彻、汤浅让二、高桥雄二。读他们的文章就像听他们的音乐,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中国作曲家中写作风格**的无疑是周文重。他的音乐作品和文章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哲学思考。他既是一位作曲家,又是一位文化学者。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久违的儒家人文精神和积极参与意识。同时,他面对当前中西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商业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具有历史学家的洞察力。
第二:本集最早的文章《走向音乐的重新整合》写于1967年。其实周先生最关心的读者是中国人。他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他与中国音乐家交流的信息。这是周先生半个世纪以来与其他中国作曲家的交流。然而,很多文章(包括几篇在英语世界被公认为经典的文章)直到今天才首次以中文向读者发布。虽然周先生英文原文的文采很难用中文再现,但我们希望至少不要曲解他的原意。
第三:周先生通过他的文章和音乐创作,仍在激励我们进一步思考,不断挑战我们。他提醒我们不要用简单的音乐标签来迎合外国人对神秘东方文化的好奇和兴趣,也不要用奖项作为艺术成功的标志来迷惑自己。尤其是他反对奴性立场,不愿受西方音乐理论的束缚或影响,创造了真正独立于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在许多中国当代作曲家取得“成功”的同时,我们应该以批判的态度问自己:我们对当代世界音乐文化的贡献是什么?有哪些新概念、新音乐素材、新技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不是模仿西方或从过去的中国音乐中回收的?哪些理念、材料和技巧能够经受住考验,并为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作曲家带来灵感?我们的思考应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是否是中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有趣、有意义。
笔者从周先生的著作中精选了18篇文章,供读者欣赏。首先向大家推荐周先生关于“单音素”和中国音乐史料的两篇经典文章,其中包括《单音素作为乐义单位:从结构的角度看音调的变化性质》(1970)以及《中国史学与中国音乐研究:我的一些看法》(1976)。可以说,“单音”是亚洲作曲家必修的公案。与周先生同时代的尹以桑、武满彻对这一概念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解释。周先生的观察视角涵盖整个亚洲音乐美学,并以电子音乐声音分析的技术语汇为参考,触及对音色结构组织的深切关注。这些观点至今仍然启发着我们当前的创作和研究。
《走向音乐的重新整合》(1967)、《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1968)、《亚洲观念与20世纪西方作曲家》(1971)、《亚洲美学与世界音乐》(1981)等,既是前瞻性文章,又是周先生的艺术宣言。周先生近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艺术路线,在后来的艺术发展中得到了确认和实现。
《风景与声音》(1990)是他对早期个人经历的回忆; 《中美艺术交流:哲学探索的实践》(1989)是他对促进艺术交流与互动的总结与反思。 《关键词是独立》(1994)、《文人与文化》(1999)、《百河汇流的黎明时代,音乐的未来在哪里?》 》(2002),《中国作曲家去哪儿? 《(2007)》等反映了周文重先生对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期待和担忧。
本书并不是周文文学理论的全部。比如周文中先生有几篇关于瓦雷兹的研究文章,但主要都是突出周先生自己的思想,所以没有收入。不过,我选择了他对瓦雷兹作品《电离》和《沙漠》的两篇分析。因为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瓦雷兹的音乐智慧,还可以一窥周文重先生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周先生对于音色结构组织的思想。
合集的第二部分是两位美国音乐理论家对周文重的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包括埃里克·赖教授对周文重先生的评论,以及宇野弥生对其的评论。浅析音乐创作与书法的密切关系
读者们一定非常关注周文中先生近期的作品。中英双语《周文重音乐作品目录》是迄今为止出版的最完整、最准确的周文重作品目录,由周先生亲自审定。选集附CD一张,收录了他近期的三首作品:弦乐四重奏《浮云》(1996)、《流泉》(2003)、六重奏(周先生称之为“双三重奏”)《霞光》 (2007)。
这部作品集的翻译主要依靠朋友们的努力。编译过程如下:作者根据译者的不同专业(音乐学、文化、作曲理论等)选择文本并划分作品。翻译完后,我负责审校英汉译文,然后蔡良宇研究员做中文润色,最后罗勤老师审稿。对选文或翻译不当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译者包括美国、英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音乐家和学者:班丽霞、蔡良玉、李亚珍、林泽雄、王路、王婷婷、周文正、邹岩。熟悉周先生英文著作的人都知道,能胜任翻译他的文章的人很少,因为他的文章知识丰富,引证有据,逻辑严密,措辞准确,意义深刻。有朋友感叹,翻译一篇文章比写一篇博士论文还费力,需要大量的学术研究。而且,所有译者基本上都有义务翻译这本书。这些朋友都不是周先生的亲传“弟子”,但他们都被周先生的坚持所感动。每当我想起朋友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我就感到非常感激。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周先生的夫人周以安女士、秘书关淑玲女士(权)、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郝光明博士()、唱片公司的布莱恩先生、乐谱出版社的吉恩先生对你们的热心帮助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哥伦比亚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支持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本书副主编、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罗勤先生。这是自2009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与西方:新音乐的诞生》一书以来,我与罗勤老师的第二次愉快的合作。想想看,这两本书非常专业。和不受欢迎的读物,而且它们决不会带来经济利益。但罗勤先生关注的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以及学术思考的深度和价值。没有他的支持和巨大的努力,我们的书就不可能问世。在此,我谨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当代堪称“文人”的音乐家中,即具有文人的独立精神和洞察力,以及使命感和勇气的人,周文中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当代文人,周文重坚持自己的独立性。现在出版这本散文集,既是为了庆祝周先生九十华诞的贡献,也是为了鞭策自己。
本书主编梁磊、副主编罗勤合影
